她有一把油纸伞

【楔子】
我收到了她的来信,当我以为她不会再回复我的时候。
信上只有短短几个字
“明天见。”
我发誓她是我见过最为变扭且奇怪的老艺术家。
住在破败不堪的小院,用着书信的方式作联系,坐在昏暗的屋子里,只有一扇小台灯开着,满地的伞骨与油纸,唯一的桌子上也堆满了画稿。
整个空气里都是油纸的淡香,有一种旧时光的感觉…
当我去的时候,她才起身沏茶,动作迟缓,又为我腾出一个小小的空地,容我坐下。
声音淡淡,茶气袅袅…
如果不是因为采访时,因天气太冷,她说话时空气中的白雾,我真的会觉得她是个死人。
天气冷的恐怖,昨日冬至刚过。她房间里的那扇古木雕花窗户还大大开着,没有空调或火炉等供暖设备,寒风从外边的院子里涌进来,带着几片从院子里飘进来看不出什么树的枯叶。

她时不时咳嗽几声,身上却又穿得单薄。
真是个奇怪的老人。
相约的采访时间结束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这片拥挤的世界,我开始起身收拾我的录音笔和笔记本。
走时,她没有送我,坐在窗前拿着那几片枯叶,似在端详。
出于对一名老艺术家的关心,我出声道:
“老师,窗户需要关上吗?”
“不必。”
当我踏出她房门的那一瞬间,这位奇怪的艺术家叫住我。
“你,你要不要听个故事…”
1
张小伞的家乡是一个无比养人的地方,钟灵毓秀。
张小伞家里做着古老的油纸伞工艺,祖上听说还蛮有声望,毕竟有西湖白娘子之类的传说,做伞的行业还算是前景不错。

但自父辈开始,西洋的铁架伞被城里的小卖部从外边运进来,货好,耐用又便宜,谁不喜欢?人们渐渐的就不再买他们家的油纸伞了。
“做伞费时间,耗眼力,特容易一辈子磨死在削伞骨的时光里。”
这话是张小伞的母亲说的。
母亲和父亲分开的早,走的时候没要张小伞父亲的一分钱,只带走了一把张小伞父亲在他们刚结婚时做的那把油纸伞。
张小伞的母亲就这样在一个冬日的清晨里走了,走的时候张小伞躲在房间里的窗户边上,往窗外哈着气,这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
张小伞听见她的母亲对她的父亲这样说,她当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她的那位做了一辈子伞的父亲没有拦住那个爱油纸伞的母亲,他未说一言,只是沉默地打开了院门,又替母亲理了理那装衣服的包袱,后来张小伞想起这个动作总是会觉得,父亲当时低头理包袱的动作,是在掩饰着那滴马上就要落下来的眼泪。

在母亲踏出去的那一瞬间,父亲叫住母亲补充了一句说:“天冷了,多穿点。”
母亲只顿了一下,便继续走远了。
那是张小伞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母亲走的那天,她的父亲坐在院子里的合欢树下,发呆,唯一的一天没有削伞骨。
她不明白,为什么相爱的人总要分开。
那一年,她10岁。
2
当张小伞到了要学习手艺准备接手的时候,父亲那里也只有一个学徒了。
那是一个孤儿,口不能言,送来的时候年龄已经半大了,茶馆嫌他不会招揽生意,又单养着一个要吃饭的,老板不愿,又在城里听见张父要收徒,就把这哑巴送来了。
父亲没什么怨言,不过是多加一副碗筷,多腾一间屋子出来的事情罢了。

他来的时候脖子上挂着的牌子,上头写了个字,张父没什么文化,又觉得和他一起姓张太过俗气,就叫他牌子上的单字:佳。
张小伞听到这个由来的时候心里定是不服的,她也觉得她的名字“小伞”太俗气了,她去和父亲争辩时,父亲也不想搭理她,任由她在一旁哭闹,而佳就在边上站着,也不来扶她一下什么的,张小伞便把他记恨上了,觉得佳是抢了父亲对她的关注。
不过她觉得有一点很好,佳想要学这制伞的复杂工序,毕竟他父母是谁没人知道,他也不小了,总要学一门手艺保身。
这个情况,张父是有了解的,有人愿意学他自然愿意教,而张小伞自是不愿学的那类。父亲倒也不强迫,虽是一同学习制伞,父亲明显对佳的要求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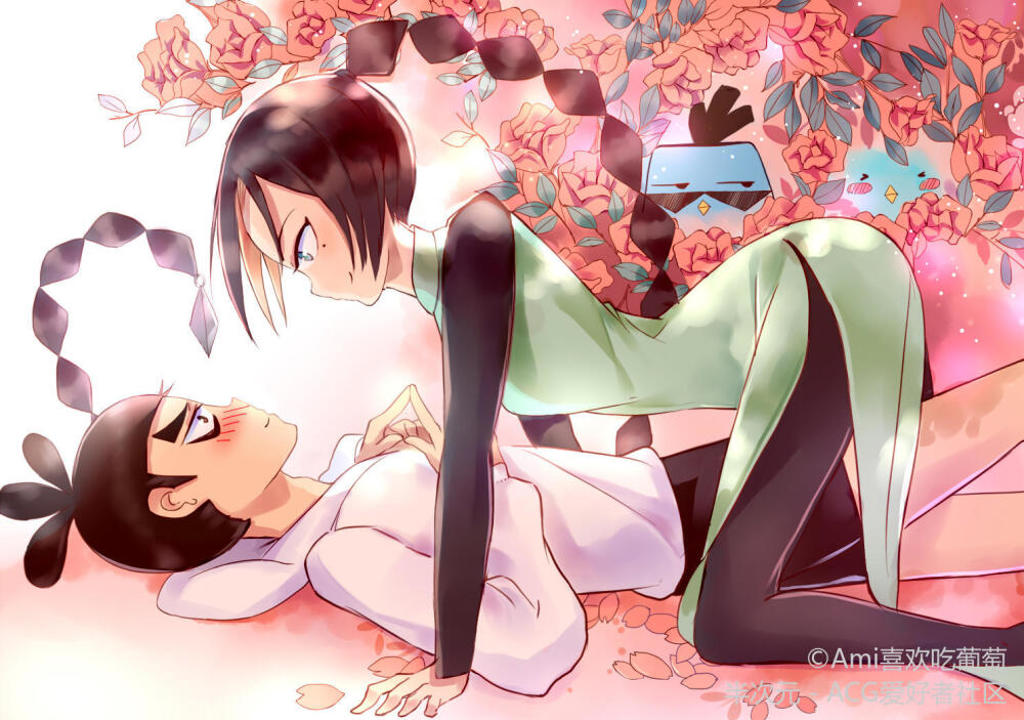
张小伞想:要是他会说话,他也肯定早就走了,谁会学这枯燥的制伞…
她跑去问佳:“佳,你为什么要学制伞呐?”
这是她在名字俗不俗事件后第一次找他说话。
佳这个时候已经很高了,他若挺直腰板,定是比张父高的,但他此时坐在合欢树前的木桩子上,正一点点的削着伞头,听到这话,他愣了一下,肩膀一抖,削掉一大块。
张小伞最近也长高了很多,站着的时候,能比佳坐着高出一个头,她见佳没有回答她,自觉无趣,嘟了嘟嘴,又推了推佳的肩膀道:“啊,佳,你个呆子!”
佳不语,他想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一个呆子啊,那你明知道我不能言语还开口做甚,岂不是更呆?
佳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嘴角上扬了一抹小小的弧度。

这一点点面部表情的变化被张小伞看见了,老实说,她从未见过佳笑的样子,就连父亲表扬佳天资聪颖时,佳也只是点头表示自己听到了的意思。
他笑起来可真好看呐,张小伞想。
等张小伞回过头来的时候,她有点愤恼,跺了下脚,再回头时瞥见那缺了一块的伞头,她嘻嘻一笑,冲屋里的父亲大喊:“爹爹,佳哥哥把伞头搞坏了!”
佳笑了笑,伸出一只没有沾到竹削的手抚了抚眉间,眼底深处笑意更深,竟是如同黑暗中突然加了一点暖色,整个人都在发光的感觉。
已经跑回屋子里躲到雕花窗子后面的张小伞看见了,也学着佳的姿势抚了抚眉间,什么也没有摸到。她觉得自己一定疯了,不然为什么会学那个呆子的动作。

那个时候张小伞还没有察觉到她对佳有一种依赖;佳也没有发现他对张小伞有着无限的纵容。
那一年,她12岁,他15岁。
3
佳要走了。
合欢树还立在院子里,花开花落竟然又过了好多年。
佳的父母来找他了,佳的生父姓叶,是距小城很远的大城里的人,挺有钱。来的那天,带着一众人,坐着一辆汽车稳稳的停在了张父的小院子门前。小城里的人哪里见过那么多好东西,都发出来了一声声感叹。
张小伞才从外边买了新的削刀回来,还没有到家就听见叶家的人到了还要接走佳的事情,她不知道为什么心中升出了一丝担心。
她在害怕,害怕佳的离去。
张小伞最近开始学习制伞了,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母亲在多年前离去后,父亲便更加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张小伞有时半夜起夜时,常看见父亲房里的油灯还亮着。

父亲在证明自己,张小伞是知道的,母亲当年走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做伞费时间,耗眼力,特容易一辈子磨死在削伞骨的时光里。”
父亲想要证明他做伞是心甘情愿的,也是心甘情愿被磨死在伞骨里的。父亲虽不说自己的身体情况,张小伞也能看出来父亲撑不了多久了的。
她能做什么呢?只能在每晚喝汤时,为父亲满满的倒上一碗而已。
张记制伞终是会让佳和张小伞继承的。
张小伞大了,她明白,自己是父亲唯一的孩子,她必须替在制伞上走了一辈子的父亲与走到半路就迷路了的母亲走下去。
张小伞突然的懂事让张父很开心,当张小伞在很平凡的一天的晚饭餐桌上说出这一句话时,他那晚一下子吃了三碗饭。

张小伞早已经忘了那些最为基本的手法,张父的眼睛也不是很好了,就让佳教授她,佳现在的手法也早就可以出师了,父亲只需要坐在院里听着自家女儿的嬉笑声,时不时点评几句,他就很满足了。
佳现在性格开朗了很多,他会在张小伞不想学制伞的时候一个人外出,回来的时候带着张小伞喜欢吃的冰糖葫芦。张父是不允许张小伞吃这些的,佳就从窗外偷偷的把冰糖葫芦给张小伞递进来,那副偷偷摸摸的样子常逗的张小伞一阵笑。
“佳,你当真是个呆子!”
这是张小伞最常说的一句话。
父亲给佳说过,让佳去到大城市里,那里机会更多,不必和他还有张小伞一起守着这个孤寂的小院子,但佳一直不肯,张父提了几次后,便不再多提了。

因为张小伞的改变,张父的身体也有了一些好转,似乎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在往好的方面飞快前行。
叶家的出现,无意打扰了这一切。
“佳!”张小伞疾步走后门回家,但她还是失望了,院里的合欢树下的那位青衣男子还是不在了。
院子前门穿来了汽车发动的声音,张小伞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奇怪的声音,她的心脏没有由来的抽动了一下,有不好的预感缭绕在她的心头…
“佳!”她跑到前门去,只看见佳坐上了那个四个轮子的怪物,然后车门又被重重的关上,发出“碰”的一声巨响。
“呆子!”张小伞看见这个四个轮子的怪物在不断的向前运动着,她有了一种预感,如果佳现在走了,他们就不会再见面了。

她开始追着车子跑,她果然是个弱女子啊,平时伪装于表面的乖张,面对身边人一个又一个的消失,她从没有过那种什么都做不了的脱力感……
她蹲在小城的巷子口,哭了一个昏天黑地,她从来没有那么委屈过。
那天夜里下起了大雨,一场在冬日里难得下的一场大雨。张小伞还蹲在路边,雨水顺着她的面庞,流入衣襟,然后又顺着衣角,“滴滴答答”的落入巷子地上的青石板上…她感到有人站在了她的旁边,雨水也远没有刚刚那么肆掠地冲刷她,她以为是佳来了,因为佳每次都这样,在她被父亲罚的时候偷偷给她打伞。
张小伞抬起头,很是欢乐:“佳!”
但她还是失望了,那是她的父亲。
“叶佳他已经走了,他本就不是这里的人,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爹…”
张小伞还是陪父亲回去了,疯了一阵也该够了。
父亲因为淋了一场雨,身体更加不好了,咳嗽的时候常有时会伴着血的吐出。
张小伞也不再乖张,她收起了所有的脾气。
她常常坐在窗边,一个人就着先祖留下来的书看着制伞的方法,愈加冷漠,愈加冷清。
“多出去走走吧。”父亲时常劝她,父亲看见她这个样子也很难过。
“知道的。”她也只是嘴上答应着,转身又回屋看书去了。
合欢树来来去去,佳走的时候和母亲走的时候季节一样,都是冬天呵。
这一年,她18岁,叶佳21岁。
这真的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叶佳,叶佳就此消失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相亲的人总要分开。
4
张小伞一路上走走停停,兜兜转转。
她走遍了许多大城市去宣扬油纸伞。她做伞的功夫也是娴熟之极,人们开始关注到这样的一些手艺人,一位在所有男性中唯一的油纸伞手艺传承的女性人物,无意是被各大杂志报刊看中的爆点。
但她奇怪的很,如果不是推辞不了,她从不接任何一个报道的要求,她只是带着她的工具,削刀,竹条,油纸…到处走,似乎在找一个人,时间久了,她也不知道她在找什么。
张父死去很多年了,张小伞没有去找人做什么法事,她找来雕刻师傅,用竹子拼接在一起给他做了副棺材,父亲爱油纸伞爱了一辈子,死后也定是想和竹子在一起的,这唯一陪伴她走的最长一段路的人,最后的一点愿望,她做女儿的,当然要满足他。

张小伞想,父亲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就是死前也没有见到母亲一面。
父亲死在冬天,因为小城里的风俗,父亲的尸骨延迟了三天下葬,三天时间,她没有闭眼的守在父亲旁边,一方面是为了孝顺,另一方面她是想见一个人。
三天转瞬即逝,她没找任何人帮让,她拿着铲子,一点一点地铲子开合欢树旁边的泥土,就这样在合欢树旁边把父亲安葬了。
合欢树陪了父亲一辈子,死后也应该陪着他。
小城里流言蜚语很多,很多人说老张死了,做徒弟的叶佳怎么说也要回来看看,真是,太没良心。张小伞听了也只笑笑,也不附和,她笑的很淡漠,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
那多嘴的人,也觉得尴尬,便转开了话题。

第二年开春,张小伞就背着她的全部身家离开了小城。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她。这年头,油纸伞之精髓:泡竹、蒸竹、晒竹、刨竹、刻竹、钻孔、拼架…做的最为不骄不躁的人,怕是只有张小伞了。
人们提起她,都说:张大艺术家,怕是真的喜欢伞吧…
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走出小城去,又莫名其妙的捧了什么艺术家的称呼,她觉得很可笑。
当她拥有一切的时候,她是个学油纸伞的废物,静不下心,浮躁的很;当她失去一切的时候,世界里只剩下油纸伞,她又成了整个业界的良心。
张小伞笑了,在颁奖典礼上,她伸出一只食指抚了抚眉间,眼底深处笑意更深,竟是如同黑暗中突然加了一点暖色,整个人都很温暖的感觉。

她呆住了,她记忆中好像有这样一个人,也喜欢垂着眼眸,用手抚眉间偷笑,像一只偷了腥的猫。
是谁呢?张小伞想不起来了。
她想的实在太过于投入,以至于连主持人的宣讲词都听得不真切。
后来,她回到了小城,看着合欢树还活着只是渐渐衰败,她突然有点开心,瞧,合欢树和我爸爸都还陪着我呢。
再后来,她有一日读书,看见扉页上有一个合欢树的解释,她的心脏漏跳一拍:
“无情树”。
读书的那日是个冬天,天气阴沉沉的,她习惯性把窗打开,窗外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但是隐隐约约还是透着点什么的,比如满园的竹条,和满地落叶,萧条的紧。
她觉得自己可能可以出家了。

这一年,她45岁。
5
“后来,这个被你们写的天花乱坠,潇洒至极的女人就呆在一个小破屋子里,还想和这些父亲留下的伞过一生……大概是那个雨天只有伞能够保护我了吧……”她说完轻轻的笑了一下,顿了顿,又补充道,“我甚至还为了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初恋做了一把伞……”
我有点愣神。
“老师,这和我听说的不一样,”我顿了顿,“你难道不是因为对油纸伞这门手艺的热爱吗?”
“我也不知道,大抵是吧。”这位奇怪的艺术家站起了身子,“我是张小伞呐,小伞小伞,我的一生就和伞分不开啊……”
末了,她又补充了一句:“我这一生,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搞不明白啊……”

这一年,她62岁。
6
再后来,张小伞死了,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在一边听着录音一边编辑着我们之前那次见面的文稿。
我初冬时见过她,没有想到来年的暮冬,人便没了。
作为一名记者,生老病死不过是常见之事。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和这位别扭的老艺术家聊过的最后一位记者,我应该去看看。
我再次去到小城,带着看望时最不会出错的菊花,然而在那条巷子口看见了一个老人,他站在张小伞的院子门口,背挺的直的很,眼珠子一直盯着那院子,他却不走进去。
我感到奇怪,走过去,叫他:“大爷,怎么不进去?”
那老头没有回答,他只是回头看了我一眼,又转了过去,盯着那屋里看。

我突然想起那个张小伞故事里的那位故人叶佳,在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初恋的故事里的男人,那个虽口不能言却有保又节操,但后来竟然变得满身铜臭味的人。
我把手里的菊花给了这个大爷,又道:“大爷,我还有事,先走了,这束菊花,您替我拿给张老师吧。”末了,我多嘴的补充了一句,“老师她…为叶佳老师做了一把伞。”
一切误会与否终要有个了断。
解铃还须系铃人。
缘起是这小城冬日窗外合欢树与油纸伞,缘灭也因如此。
张小伞死在冬天,合欢树也真的死了,枯叶一地,无人打扫,萧瑟又冷清,小城里的好心人把她和父亲埋在一处。
他们一生都为了那把伞而奔波,死后也定是要同那把油纸伞一起的。

张小伞死前安排好了一切,所有有关油纸伞的书籍和工具都捐给了大城市里的油纸伞工作室,手艺终归还是要传承下去的。
后来我听说,她死前躺在床上一直不让关窗,而且吵着要吃糖葫芦,就和一个孩子一样。
我发誓她是我见过最为奇怪又变扭的老艺术家,也是最为令我映像深刻的一位。
那一年,她63岁。
【后记.叶佳】
我叫叶佳,我是一个懦夫。
我15岁那年来到张家,随张小伞的父亲张先生一起学习制伞。
我的身世很苦。我听茶馆里的伙计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被人从外面抱进小城里,刚开始时店里缺少人手,老板便想着让我来替一段时间。后来人手够了,我又不能言语,不懂招徕顾客,木头桩子一样,赶走了便是。好在老板还有良知,知道帮我寻一个去处。

后来遇见了张小伞,她说我像呆子,我也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呆子。
我能做的只有学习做伞,我懂事懂得早,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说:学一门手艺才不会被别人所看不起。我不希望别人看不起我,学制伞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我21岁时,叶家来寻我,张先生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愿意回去。
我不想一辈子和张先生一样,呆在这个小城里,做着一把油纸伞,我想要出去。
所以啊,我走了。
毕竟张先生给我说过当年师母的那句话:
“做伞费时间,耗眼力,特容易一辈子磨死在削伞骨的时光里。”
我不想这样。
张小伞一直在找我,我是知道的;她的制伞技艺越来越好,我也是知道的。

有一天,小城里有书信传来,我这才得知,张先生去世了的消息。我的父亲唏嘘几声,也没再多说。
我那时是在干什么?哦,对了,在父亲给我请的先生那里学习,不是学习油纸伞的制作,而是学习如何挣钱等等诸如此类。母亲她老了,生不出孩子来了,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思来想去,还有我这个从小走丢的叶家大少爷,便把我接回来,想让叶家百年基业长青。我后来想起,觉得简直可笑至极。
那也是后来了。
等我忙完一切回到小城,走过那条小巷,看到院门大大开起,合欢树独自屹立在院中,落叶遍地,却无人再去打扫的那一瞬时,我后悔了。
张小伞早走了,听老街坊说,她张小伞就只是背着她的全部身家就离开了小城,去了远方。

她去了哪里呢?没人知道。
再后来,父亲母亲相继离世,我也成了和张小伞一样的孤独的人。
我只能自己骗自己,我在我城里的大房子里的院前也种了颗合欢,但是不知怎么的,终归是不如张小伞院子里的那颗长得好的。也许也没有多好,只是我的记忆美化了那棵合欢而已…
那究竟美不美呢?我记得不真切了。日子过得太过于久远了啊,
我时常回忆起我们曾经年少时,坐于合欢树下,一起削竹条的情形…
“我大抵是老了。”我想,越老越喜欢回忆过去了啊。
我常去看张小伞的新闻报道,我知道她过的很好,这就足够了。
后来她得了奖,全城都在传她的佳话,人们像我提起她,都说:叶先生,您是张大艺术家的师兄吧,张大艺术家怕是真的喜欢伞吧,她可真厉害……

我一般听到这些话,会笑笑,不置可否的模样。其实心里却在想:她张小伞,哪里是喜欢伞,人家喜欢的是糖葫芦。
想到这里时,我的心脏竟然有一点抽疼。
后来听说她回了小城,想安心做一辈子的伞,安心呆在那个雕着古木窗花的小屋里,削一辈子竹条,真真正正地做到把一辈子的时光磨入伞中。
后来的后来啊,我们都老了。
有一天,我听说有人要捐赠东西,捐到我投资建的大城市里的油纸伞工作室,所有有关油纸伞的书籍和工具,都捐。我听见有人这么说起时,神使鬼差般我去看了看那些东西。里面有把削刀我很熟,那是我15岁那年削掉伞头的那把削刀,有点掉漆。
你瞧,这么多年过去了,就连铁也生锈了不是……

捐赠人没有署名,但是我知道,那是张小伞的。她其实身体也很不好了,坐着做了一辈子伞,膝盖骨受不了,疼痛也是常态。
后来我回想起这事,她到死都还想着要把这门手艺给传下去,她还是那个的张小伞,削刀削走了她的时光,却削不走她的无上美好与单纯。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能成为一位老艺术家的原因,而不是和我一样浑身铜臭味。
我觉得我有点可笑。
我66岁生日那年,张小伞死了。我这一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盼,我把我们叶家做到家大业大,但我终生未曾娶妻生子。
城里人私下讨论说我是个怪人,不爱那西洋的折伞,偏爱那江南小城里的油纸伞;不爱这荣华富贵与世间美人,就连遗产也早早决定在死后就捐给手艺工作室…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谁不爱那荣华富贵,当年那个21岁的男孩他也爱啊,只是到了多年以后他才发现他一直找错了,爱错了罢了。
我收拾好我的一切物什,我听见我说,“叶佳,你得去找张小伞。”
我佝偻着腰背,站在巷子口,往巷子深处望下去,没有看见那个笑意盈盈的姑娘,却似乎可以听见她叫我“呆子”的轻盈的声音。
我一时间有点被时光砸懵的彷徨感。
我走到院子外,却又不敢进去,我透过院门上以前挂锁的小孔往里边看,一如多年前我刚来时想找落脚处时一个模样,只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
有位女子叫住了我,她问我怎么不进去。
我不知如何作答,也对,我本来也口不能言。

她竟又叫出了我的名字,叶佳。
她说了什么?
张小伞,她为我做了一把伞。
我一时间有点心急,我拿过她手上的花,连向示意道谢也没有,我推开屋门,疾步走了进去。
也不能说疾步,我一个66岁的老头,哪里来的什么疾步。
我望见合欢花开了花,张小伞还是那娇俏可人的模样,张先生也还健在,满地的竹条竟是那样熟悉。我好像返老还童了。
我走进张小伞的那间屋子,天气冷的恐怖,昨日冬至刚过。她房间里的那扇古木雕花窗户还大大开着,没有空调或火炉等供暖设备,寒风从外边的院子里涌进来,带着几片从院子里飘进来看不出什么树的枯叶。
桌上有一本翻开的手记,上边夹着一片道不出名字的叶子,上头最新的一句话是:制伞是孤独人无尽的悲伤,我以时光为代价,融入这伞骨……

独倚幽窗,看转角处的青石小巷,一柄久违的油纸伞,遮住了低过屋檐的光阴。
是什么溅湿了字迹?
再后来啊,我住进了我那建在大城市里的油纸伞工作室,有一天,有个小姑娘来敲门,想拜我为师,我递了张绢纸给她。
上头写着:“做伞费时间,耗眼力,特容易一辈子磨死在削伞骨的时光里,你可愿?”
我如愿听到了那少女清脆的嗓音:
“我愿!”
当雨滴与泪滴相提并论 ,油纸伞仍守着灯火黄昏。
我会带着这两把伞沿着这青石板路走下去……
 用卫生纸制作一个假j
用卫生纸制作一个假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