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程鑫|《杀死胶片里的麦穗》

-ooc
-4.2k
-伪骨科警告
推荐搭配BGM:Ólafur Arnalds《saman》
母亲给我传来一张电子机票的截图时,还以为她想出了什么新法子劝我回家。
我和她的聊天界面只躺着她发来的那张略显孤单的机票截图和附带的一条短信。我逃到奥克兰,满打满算也有三年了,扔掉了从国内带出来的sim卡,屏蔽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鬼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在美国的号码的,还发短信,说丁程鑫考上了加州大学,让我好好照顾他。
她生怕我还有一点用处没被她榨干。
我点开截图,把手机扔到桌子上,一边握电子笔在平板上描草稿,还得一边腾出精力往手机上瞟。
明天下午落地的航班,北京飞奥克兰,乘机人那栏写的是丁程鑫的全拼。
我把手里画了一半的草稿保存,从一旁的抽屉里翻出有些陌生的马克纸和碳素铅笔,想着丁程鑫的名字,在纸上拟出了大概的轮廓。
眼睛,鼻子,嘴唇。
铅笔在马克纸上来回摩擦——我记得丁程鑫的下唇很饱满,像水滴。

笔尖磨平粗糙的颗粒感,我把他的嘴唇画重了,看上去像被不知道哪个涂了唇釉的女人亲了一通,嘴角全是晕染开的印渍。
看得我不爽,翻了半天也没找着上次用剩下的半块橡皮。
桌上的手机震动了几下掉到地上,我以为是编辑又来催稿,大半夜打电话吵我这事他常干。我按下接通键,想没好气的怼他几句脏话,听筒里传来的电波频率却震红了我的耳朵。
“姐。”
我记得小时候丁程鑫都是规规矩矩的喊叠字,怎么长大了倒变懒了。
我开了免提,盯着屏幕上显示的电话号码,手指切换到短信界面,看着电话号码的重叠,心里猜了个大概。
“妈没找到你的电话,明天,忙吗。”
像是生怕我挂掉电话似的,丁程鑫前半句话说得飞快,再快些就听不清了,后半句倒含含糊糊的,声音闷闷的,磨叽半天才吐出前两个字,隔了几秒才说完一整句。
我故意捡起被搁置在一旁的铅笔,把手机放到纸的旁边,对着话筒画着简单的直线和竖线。
等电话那头传来清晰的呼吸声和关门声,我把通话切换成了Facetime。

丁程鑫应该是还没反应过来,手机架在台灯前,屋里也没开灯,看样子是刚洗完澡,他靠在椅背上,脸上还盖着一条白色浴巾,看不清脸。
怪不得讲话闷闷的。
“丁儿。”我把手机立在素描本前,想让他把浴巾扯下来,和我画的草稿对比一下。
丁程鑫不是我的弟弟,各种方面的不是。
他是忽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的,是母亲再婚的那年,继父带他进门的,算半件聘礼。
我过生日那天,继父拎着他和生日蛋糕站在门前,对,拎着他。那小家伙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穿着哈利波特的斗篷,戴着一副没镜片的黑框眼镜,手里乱挥着从路边捡来的木棍,一点都不可爱。
所以第一次见面,丁程鑫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那个拎着他的男人也是。
继父那天穿的是西装,乍看上去彬彬有礼,但是露着线头的劣质布料和被胡乱塞进裤子里的衬衫暴露了他。
瞎子都能看出来,他和我母亲之前遇到的男人没差,冲着钱来的,就是会装,跟她谈什么情呀爱呀,再贷款买个几克拉的钻戒,翻翻日历挑个好日子求婚。
这套招数对小姑娘都不见得好使,偏偏我母亲看不清。最后买解戒指的贷款是她还的,他俩住的房子,开的车,都是母亲前几年付的全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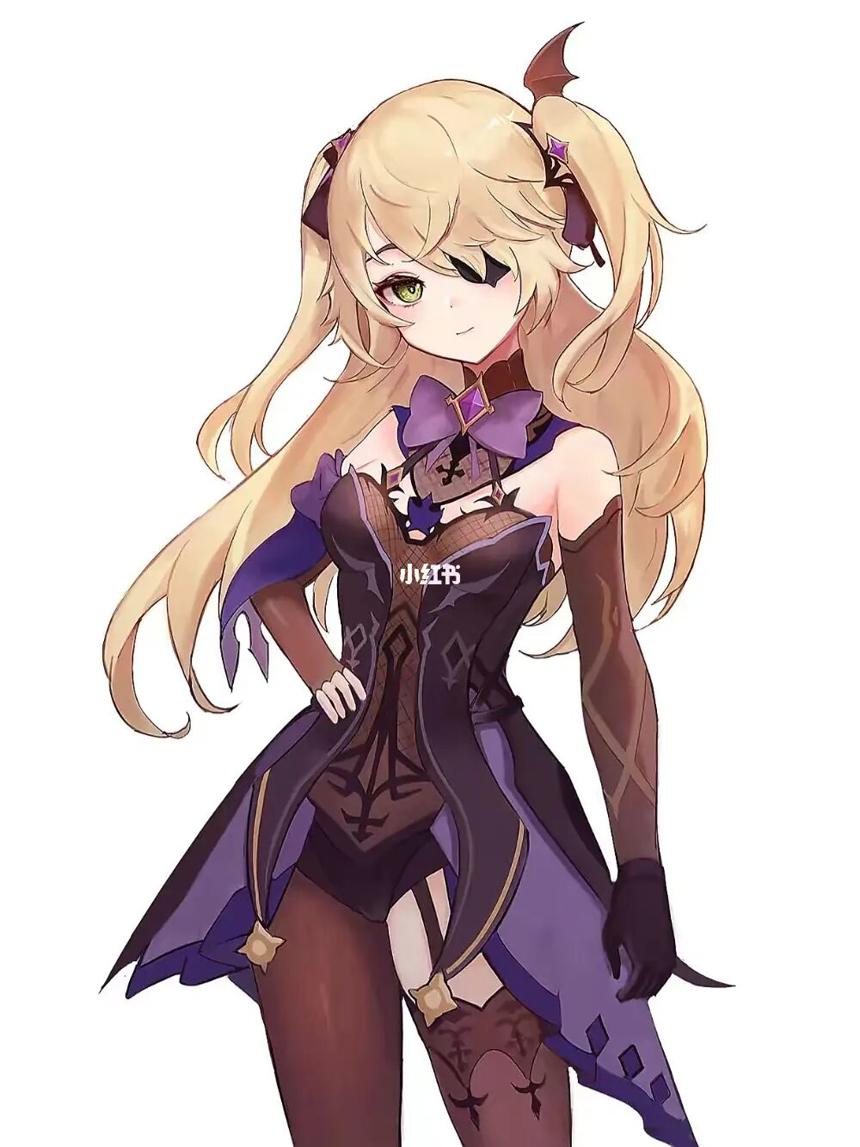
切蛋糕的时候,母亲举着手机再一旁录像,之前也没见她这么有仪式感过,多半是因为他在。
继父把手搭在我握着刀的手上,拇指轻轻摩擦我的手背。
我想把手抽出来,他死死摁着我的手,脸上挂着一成不变的笑。
蜡油滴在我的手背上,烫的我红了眼眶。
那天我的头发上沾了很多奶油,扣子也扯掉了半个,我想我也没给丁程鑫留下好印象。
又怎么样呢,那时候的我想。
我把年初攒的钱拿去报了雅思,瞒着母亲考试,背着她申请了国外的大学,然后逃到加州,再也没和她联系过。
和丁程鑫也是。
屏幕里的丁程鑫伸了个懒腰,椅子也嘎吱嘎吱的响,我撑在桌子上看,想着明天把他的房间收拾出来,再给他挑把新椅子。
丁程鑫还是盖着那条浴巾,头发应该是没干,浴巾看着有点湿,隐隐约约能看出他的唇型,特别是下唇。
有那么几秒钟,我真的很讨厌所有白色浴巾。
我关掉了摄像头和免提,把听筒放在耳边,手里握着铅笔,在草稿上原本画重了的嘴唇边指出了个箭头,写了一串字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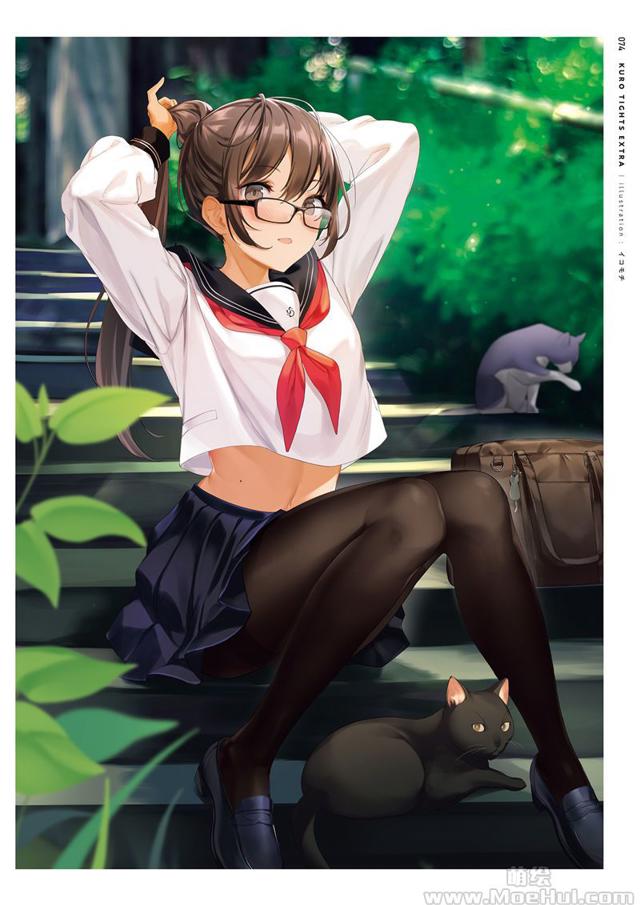
“明天我去接你,机场。”
好像是讲了两遍重复的话,也好像没有。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我想起来丁程鑫学的是心理学,猛的踩了一脚刹车,把导航路线换成了最远的那条,顺便给丁程鑫捎了张新的sim卡。
我那天带了相机,其实不是为了记录什么,我对那些久别重逢的偶像剧情节不感冒,也没心思研究现在小男生喜欢什么样的欢迎方式,只是带我的美编让我拍点日常发给公司,到时候剪出来放到网上,美其名曰多领域发展。
我的饭碗握在她手里,我也不好拒绝。
丁程鑫拖着两只黑色漆皮的行李箱,从国际到达厅的B口慢慢腾腾的走出来,我正好站在他对面的滚梯上,中间隔了几缕阳光。
我以为丁程鑫的十八岁会和我的如出一辙,平凡、普通,甚至滑稽。
我逃到奥克兰的时候也是十八岁,穿着皱皱巴巴的短袖,原本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也在长途飞行中弄丢了发圈。
过海关的时候,我攥着装着护照和机票的透明袋,行李箱被检查人员翻得乱七八糟,身后是我听不太懂的催促声和轰轰的空调声。
刚下滚梯的时候,我接到了丁程鑫打来的电话。

他靠在标着Exit B的柱子上,一动不动的盯着手机,看累了就摘下金丝眼镜揉揉眼睛,还没穿过阳光,就知道他漂亮得像一尊雕塑。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从包里拿出以前不常用的香水,算沾了点味道,然后从丁程鑫面前走了过去。
我靠在柱子的另一边,翻出手机随便点开了某个界面,其实哪条帖子我都没停留。
我听到了行李箱车轮滑过地板的声音,下一秒,丁程鑫抽走了我的手机:“姐,什么时候换的香水。”
丁程鑫之前送过我一瓶香水,托我朋友送的,还以为我不知道。
丁程鑫很了解我,里里外外,各个方面。
香水的名字是可可小姐,双重名字,双重性格,感性的琥珀香调,掺着柑橘、广藿香与香根草。
官网上的创作灵感写着这样一句话:
可可小姐,献给慧黠叛逆,恣意随性,时刻真实面对自我、释放难挡魅力的女性。
自由而大胆,任性而诱惑,我想这是丁程鑫眼里的,或者幻想出来的我。
我没敢看他的眼睛,也没想夺回手机,只是隔着口罩喃喃地说:“之前的香水和我不太搭,所以换了新的。”

丁程鑫把手机放回我的兜里,问我是不是不喜欢。
我忽略掉他的问题,侧过身想接过他的行李箱。
丁程鑫把箱子拉到另一边,我扑了个空,而他虚环着我的腰,漂亮的手指蹭过我的脖子,口罩贴着我的耳朵,呼吸声也比电话里听的更真切。
“姐。”他只是叫了叫我,丢掉了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
我把新买的sim卡塞给他,丁程鑫当着我的面把旧的号码扔进了垃圾桶。
丁程鑫太了解我了,像我亲手种下的麦穗,需要他,依赖他,心甘情愿的围在他身边。
所以我有时候会把心理学和读心术画上等号。
加州的房价不低,租下市区的一居室,几乎把我的工资抽走一大半,钱包里只能剩下几张一百刀样式的绿色钞票。
丁程鑫来之后我也没打算换房子,只能给他往地上多铺几层被褥当作歉意。
我坐在床上,看着丁程鑫不紧不慢的把衣服挂进我的衣柜。
“要不要给你买个新衣柜?”我低着头,想把头发解开,结果发圈脱落掉到地上,俯下身捡时,我亲到了丁程鑫的鼻尖。
我的发丝落在丁程鑫的脸上、眼镜上、手腕上,他的呼吸涌向我的嘴唇,温热而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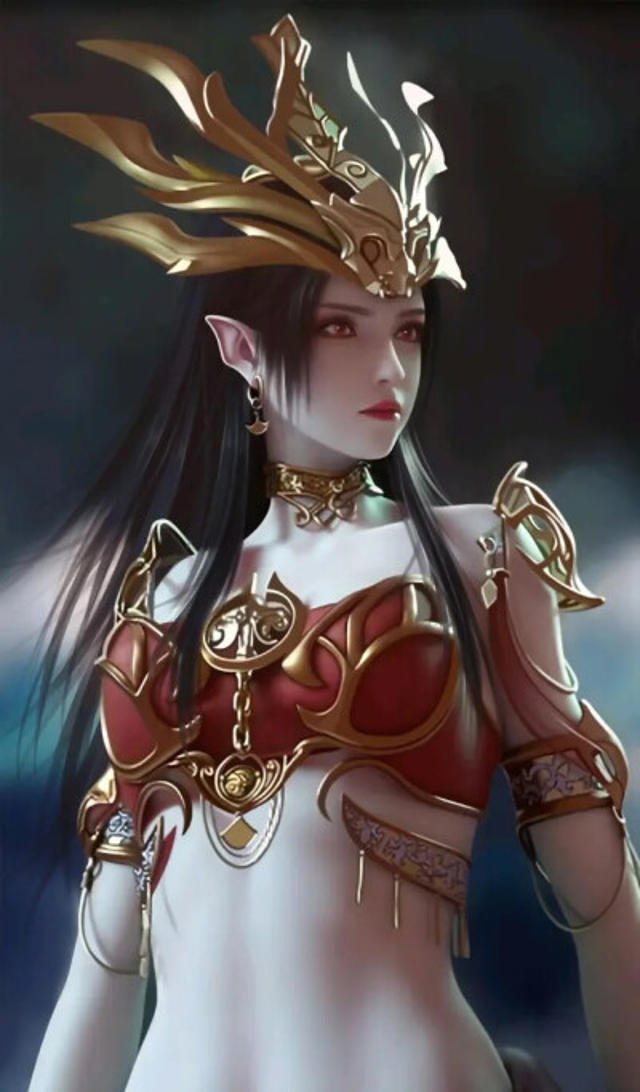
“姐,骗我呢,你没换香水。”
他闻了闻我,也吻了吻我。
潮汐起伏的海水没有尽头,我和丁程鑫也是,我们深刻、翻涌、滚烫。
有几个喘息的间隙,我会咬丁程鑫的耳朵:“星星,留一件短袖给我吧。”
那天我胡乱关了灯,看不清他的眼睛,只是挂在他发梢的汗会偶尔落下。
有时人会偏心于模棱两可的答案,比如我,比如我和丁程鑫。
比如动静太大时,我会扯谎说最近家里养了猫,回房间的时候丁程鑫就委屈巴巴的藏在桌子底下。
再比如丁程鑫偶尔的恶趣味,前 戏喜欢抓脚踝。
不过他白天的时间都用来忙大学里的研究项目,我窝在家里被美编催稿,偶尔被拉出去拍几帧符合大众口味的视频,然后光着脚等丁程鑫回来,等他回来踩他的皮鞋,播放早就选好的黑胶唱片,随着音符跳舞。
“我们像两只落单的袜子。”某天丁程鑫忽然吻在我耳边。
“莫娣里的台词吗。”
他点点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
丁程鑫走之前都会给我留下一件短袖,他穿过的,如果我睡醒的时候正好他还没出门的话,他会给我梳好丸子头,再答应我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一罐新的油彩。

他还特意新买了一个冰箱,专门放油彩的,离餐桌很近。
丁程鑫偏爱氛围感,缠着我买了几支蜡烛,要做烛光晚餐。
所以趁他做饭的时候,我就打着手电筒,在墙上用他新买的油彩描出星星的样子。
后来墙几乎被占满了,我心血来潮把它拍下来放到网上,被人看中,联系了带我的美编想花高价买下来。
我摆摆手拒绝了,在中间牵线的美编脸色不太好看,大概是因为她没法拿到买家拟的合同里标着的5%的费用。我没太放在心上,只是后来我交的稿子都一一被否决了。
原本负责我的美编拉黑了我的联系方式,出版社也甩给我一份冷冰冰的解约合同,甚至连违约金都闭嘴不提。
我捧着一摞厚厚的纸,看着上面空空荡荡的,不知道画些什么,简单描几根线条就把它们扔到地上,房间里的窗户开着,乱糟糟的线条被风卷跑。
丁程鑫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帮我捡起那些连草稿都称不上的涂鸦了,他把着我的椅子,把我抱起来,轻轻抚摸我的蝴蝶骨。
我告诉他,画星星,其实是在画你,画那些我开不了口的、泛滥成海的爱欲。

“我考下驾照了,姐,一起去海边吧。”丁程鑫坐在床边,把我抱在怀里,闻我脖颈间的香水味,捏我新做的美甲,吻我的手背。
一起逃吧,可可小姐,一起逃吧。
怎么形容我和丁程鑫,像两个接吻的人,身后是拉扯着我们的无数双手,企图把我们分开。
但我们的距离是负数,没有间隙。
我和丁程鑫逃到西海岸,他点了一团火。
我把眼镜忘在车里了,重新戴上才看清那团亮是火堆。
“别去取了,能看清我就好,离我近一点。”
丁程鑫把我拉近,给我系上了一半项链,另一半在他脖子上挂着,两枚吊坠拼在一起是一整颗心。
项链带磁力,只有我们接吻的时候会撞在一起。
我是心甘情愿被你的爱困住的,丁程鑫说。
我们出逃的最后一个月,丁程鑫写完了他的论文,主题是麦穗定律。
“人总认为自己会遇到更好的人,就像他们总认为下一个长出来的麦穗才是最好的。如果永远成为下一个麦穗,人是否会对他保持如一的热忱。”
结尾是句号,丁程鑫已经得出了他的肯定答案。

跨年的时候我带丁程鑫去了纽约,在时代广场等倒计时。
丁程鑫忽然掏出一只耳机塞给我,电流随着耳机线传入耳膜,是在家踩着丁程鑫的皮鞋跳舞时的曲子。
倒计时在繁华的楼上不断更迭,一直到零,人们欢呼,而我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能通过嘴形辨析出丁程鑫的话。
“加州会下雪吗?”
他又向我抛出了个问题。
“会,我们也没有那么小的概率会相爱。”
 祺鑫纯车吃丁程鑫红豆
祺鑫纯车吃丁程鑫红豆















![[丁程鑫X你]丁程鑫的手到底好不好牵](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323/161035_34911.jpg)
![[丁程鑫X你]丁程鑫的手到底好不好牵](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323/163354_80226.jpg)
![[丁程鑫X你]丁程鑫的手到底好不好牵](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408/153338_26891.jpg)
![[丁程鑫X你]丁程鑫的手到底好不好牵](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601/171249_9983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