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时代的小人物之主父偃(三)左右开弓
2023-05-30 来源:百合文库

主父偃凭借着自己卓越的才能和皇帝的赏识登上了人生与事业的顶峰。但这一切也还只是开始,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反正哪里热闹,哪里就能听见他的声音。
比如汉武帝的后宫,当时就很热闹。自皇后陈阿娇在元光五年(西元前130年)被废,中宫的位置也就空了下来。而后宫佳丽之间此刻最得皇帝宠爱的就是卫子夫(后来的大将军卫青的姐姐),武帝也一直有意立卫子夫为后,但不幸的是卫子夫出生不好(是个歌姬)、血统不高(僮仆之女)。而汉朝尤其重视门第和血统(比如曹操,血统高贵的袁绍就骂他为“阉宦遗丑”;再如刘备,都落魄到织履贩席了也不忘坚持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所以卫子夫当时的条件恐怕只能去评选“超级女声”,立为皇后就诚然不容易为“舆论”所接受,因此武帝的这一想法也就只好被暂时搁置。
说了那么多其实此事原本与主父偃八杆子都打不着(他不是管礼仪的太常),他完全没有必要去淌这趟浑水,因为但凡牵涉到此类宫廷事件而表现出了自己的态度都无异于博弈(比如反对唐高宗李治立武则天为后的人,后来都被武则天整的很惨)。但是主父偃并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挥舞着荧光棒对卫子夫表示力挺。

究其原因和动机史书上没有详载,兴许有人会认为主父偃这次不过是在逢迎媚上,但我觉得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第一,应该不能排除他逢迎媚上的成分,反正谁当皇后对自己都没啥影响,挺谁不是挺,那还不如挺皇帝喜欢的。
第二,汉武帝正为反击匈奴着重培养一批将领,而卫子夫的弟弟卫青也在元光六年以骑奴之身拜为车骑将军并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初露峥嵘(长驱直入一举捣碎了匈奴的圣地龙城),这就很让主父偃惺惺惜惺惺。不难看出,卫青将逐渐成为汉匈战争的将星,此时若立卫子夫为皇后则无疑是对卫青的最大鼓励。
第三,卫子夫也是以微薄之身挣扎着走过来的,其间遭遇也就难免让主父偃多少产生点同病相怜的感觉,并愿意为她登高一呼。不就是出生不好、血统不高么?孝文窦皇后不也是出生贫苦人家,现在的王太后(汉武帝生母王娡)还是二婚呢,这又怎么说?
当然以上三点纯属个人猜测,但不管怎么说,卫子夫终于在元朔元年(西元前128年)争气地为汉武帝诞下皇长子刘据,并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中宫之主。事情到此恐怕也只好算做主父偃闲来无事而进行的一次公私兼顾的博弈,所幸的是他又成功了。

此时的卫青也终于不负圣恩,迅速将感激成功地转化为奋勇杀敌,于元朔二年(西元前127年)率军赶走了盘踞在阴山以南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并自秦朝后又一次占领了河套平原。举朝上下庆贺胜利的同时,这片土地的处置问题也就抬上了议事日程。
最先发言的当然还是主父偃。他认为河套地区土地肥沃(素有小江南之称),而且有黄河天险可阻敌于外,秦将蒙恬就是以此为据点北逐匈奴(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运输补给交通便利,那是开疆僻壤,剿灭匈奴的战略要地(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因此应当筑城以戍守。但出人意料的是满朝公卿都表示反对,而反对声中最响亮的,就属御史大夫(三公之一,负责监察)公孙弘。
这公孙弘是个什么人呢?他貌似忠厚,但城府极深(“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史记》),“玩心眼”和“和稀泥”是他为人处世两大准则。先说“玩心眼”:他经常和主爵都尉(主管爵位的封赏)汲黯一道请见武帝,然后总是让汲黯先开口以观察皇帝的神情(看皇帝高不高兴听)然后再进行补充。他那些迎合上意的建议当然就更容易被采纳,皇帝也就自然而然与他越来越亲近。再看“和稀泥”:就是他与同事们事前商定好的事情一到了皇帝面前,他都能背弃事先的约定顺着皇帝的心思发表看法。汲黯最后忍无可忍,就在朝堂上指着公孙弘说:“这个山东佬太狡猾了,上朝之前还专门来找我们确定统一意见,现在却出尔反尔,我看他不是个忠臣。”公孙弘就找皇帝辩解说:“那些了解微臣的人认为我是忠臣,不了解微臣的人就把我看作是奸臣。”算是蒙混过关,皇帝竟也相信他的鬼话!

而且此后越是有人告他的状皇帝就越器重他。
靠着这两大法宝公孙弘步步高升爬到了御史大夫的位置,反正主父偃这个建议他们又是统一了意见要反对的,因此公孙弘也就本着“全心全意为纳税人着想做好行政监督工作”的原则引经据典,说秦朝当年动用三十万众去修筑朔方城,最后也没成功,还是把它丢弃了(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认为不该劳民伤财地去经营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争议一时僵持不下。
汉武帝倒是赞同主父偃的建议,不过出于对公孙弘的尊重他并没有乾刚独断地当即拍板,而是唆使侍中(皇帝的高级顾问)朱买臣去反驳公孙弘。公孙弘十问十不知(既然皇帝反对,就算知道也不能说),只好认输说:“臣就是山东的一介乡巴佬,难免目光短浅,现在终于明白过来,那就把建设部的预算都投资到朔方吧。”才算下了台阶(又是和稀泥)。于是汉武帝便在那个地方设立了朔方郡,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又重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这一回主父偃算是把公孙弘给得罪了,不过他倒并不十分在意,反正迟早是要得罪的。因为但凡得皇帝器重威胁到公孙弘地位的都被公孙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个董仲舒,就被公孙弘逮住个由头打发到不太好合作的胶西于王刘端那里做国相去了。这一点主父偃未必不明白,但他根本就没想过要与公孙弘一般见识,兴许公孙弘这号人他打心眼里就看不起,因为对于主父偃这类纵横家而言,做事比做官要稍微重要一些。

除此之外,主父偃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检举。比方燕王刘定国干的那堆破事,就是他揭发出来的。
刘定国又是个什么货色呢?禽兽不如。禽兽不如到什么程度呢?他先是与后母通奸生下来一个儿子,并且还把他弟弟的的老婆也夺来收为姬妾,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个禽兽居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放过,燕国的三个翁主(诸侯王之女称为翁主)竟轮流陪自己的父王“睡觉”……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事!这种人当然不得好死,主父偃也算是为自己在燕国所遭到的冷遇着实地出了一口恶气。
但如果你要认为主父偃道德有多么高尚、作风有多么正派、多么嫉恶如仇那可就错了。因为他除了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外,还摊上了受贿。
自燕王刘定国伏法后,主父偃越发热衷地发奸擿伏(比如那个董仲舒认为灾异是上天对皇帝的警告,可是草稿还没打好,就被前来拜访的主父偃偷去呈给皇帝,差点没把董仲舒给害死),反正他今天检举这个,明天揭发那个……吓得那些个同僚们都纷纷用贿赂去堵他那张嘴。主父偃或许是年轻时穷怕了,反正他来者不拒。谁的钱他都收,谁的钱他都敢收,短短几年就积累了千金家财。弄到后来连他的管家都觉得有点过分(人或说偃曰:“太横矣。”),这才引出了主父偃那段伤心的话:“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史记》),而这段话却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话的前半段主要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这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后半段中的“五鼎”是祭礼的一种级别(《春秋公羊传》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后也用来指吃饭的排场,与之对应的“五鼎烹”是指受刑的排场。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大丈夫活着的时候没能享受到‘五鼎食’,那死的时候就应当追求‘五鼎烹’。”这就简直与后来东晋桓温的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晋书》)如出一辙。反正无论生死都要享受到“五鼎”的待遇,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总之绝不能以碌碌之身遁于史册。这就是主父偃的价值观,也是所有纵横家的价值观。至于“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之类的话,春秋时吴国的伍子胥说过,现在主父偃把它转载出来亦不过是为自己的“贪贿有理”作一番开脱。
尽管主父偃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无耻,但难得的是他至少他敢把无耻的话公开的说出来,并且还说得掷地有声。我们现在不妨将此时的主父偃与他曾经走过的路联系起来回顾一下,便不难找出其中更深层次的缘由。
一个人活着,总得有点什么目标,支撑着他不至于因厌倦生活而提前退出舞台。目标有大小,有远近。小的、近的如为一顿饭操心劳神,大的、远的如坐在菩提树下去冥想普度众生。在众多目标中,做官相信许多人都不会讨厌的。好些人的目前目标之所以不是做官,那是因为力有大小,势有高低,机遇不常来。余岂不好乌纱帽哉,余不得已也!不过,虽然他们的注意力暂时为别的目标所吸引,但心中的一个远大目标早已巍巍矗立,根深蒂固:即便这辈子不能如愿,拼了命培养儿子也一定要捞个一官半职。

那么敢问诸公,做官干什么呢?是啊,干什么呢?在主父偃这里,就简直不成其为问题。他回答得干脆极了,“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貌似深奥的问题在他那里迎刃而解,做官除了能实践自己的治国理念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五鼎而食”。
“五鼎食”是官本位社会里生活的高级境界。开饭时一溜儿摆开五口青铜大鼎,宰牛烹羊,热气腾腾,香味馥馥。主客边听高雅的编钟打击乐边猜拳行令,一旁美女温柔伺候,空气中洋溢着甜丝丝、暖洋洋、晕乎乎的气息,此乐何极!钟鸣鼎食,这是成功人士的标志,上流社会的缩影。好比今人请客,动辄去五星级酒店,那岂是你我凡夫俗子能玩得起的!“五鼎”也好,五星级酒店也罢,都只是一种符号,指代的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一旦你和这些符号划上了等号,那就恭喜恭喜,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不敢再来纠缠你了。
主父偃在梦里吃了多少回“五鼎食”,只有天晓得!想他当年醒着时肚皮饿了就是想吃一顿饱饭也得要费点周折。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富贵的亲戚、没有发迹的哥们,种不得田、织不得布、舞不得刀,虽说立志要将肚子里的那点《春秋》、《易经》之类的才学换回一顶乌纱帽,但货没有出手之前,他便屁也不是,只会也只能张着嘴白吃饭。这样的人多么讨嫌!从他的家乡齐国,到燕、赵、中山,再到国都长安,凡他脚印印到的地方,接待他的除了白眼、冷遇,就是排挤、侮辱。东奔西跑了四十多年,他连个陶碗都端不稳,更不用说那五口壮观的大鼎了。

就在他最后放手一搏的时候,一直心不在焉的老天终于注意到他。因为给广揽贤才的汉武帝上书言事,他被皇帝召见并拜为郎中。通向“五鼎食”的门好不容易开了条缝。加油,加油,继续努力!只一年的时间,他四次升迁,官至中大夫,皇帝对他十分器重,“五鼎食”的人生目标终于得以实现。
倘若认为“五鼎食”的内容仅只是吃点、喝点,那未免幼稚得可爱。在一个集权的制度里,拥有权力的好处是不胜枚举的。大权在握,第一要务必定是进行权钱交易,为自己聚敛财富。否则,只凭自家的俸禄,那五口大鼎能不能天天升起热气都是个问题。第二呢,那自然还要抖一下威风,快意恩仇,先前那瞧不起他的人就得为自己看人低的狗眼付出代价(后篇有叙)。第三,第四……纵马驰骋,有权的感觉真爽!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知识分子,虽然非常瞧不起商人,但却不知道自己实际上也是商人,卖与帝王家的虽是所谓的治国良术,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却与一般商人别无二致。因此在没有健全的政治社会机制和权力监督约束的环境里,皇帝严刑峻法、砍头灭族的杀一儆百也只是枉然;号召这群“商人”加强修养、提高素质就更是扯淡。只要有机会,主父偃之流的“商人”总要挥舞权力这根魔杖获取更多的好处。面对着这个强硬的政治老手,大家只有争相巴结他。大把大把的钞票蜂拥而入,烧得主父偃那五口大鼎的热气越冒越大,香味越冒越浓。

这些自然都让主父偃十分快乐。但是快乐有没有可能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呢?放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若是放在官场中,答案似乎又能一眼看穿。
因为要维持“五鼎食”的场面,扩大“五鼎食”的规模,就不能不四处伸手。哪怕最昏庸的统治者,都不能容忍官员把手伸得过长而掏空了自家的江山。一旦臣子逾越了容忍的底线,就会将他“五鼎烹”了以儆效尤。另外,在一个官由上授的等级社会里,上司的好恶决定了下一级官员的运动轨迹。每一个为官者都只不过是专制体制中的一枚棋子,全凭上面的“国手”主宰命运,一旦将你拿出棋盘,快乐也就到头了。主父偃虽一时间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但他商人的本性决定了他的手不会干净,棋子的属性注定了他的命运操纵在皇帝的手中。那么,他的快乐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五鼎烹”的结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主父偃不是个读死书的呆子,又有那么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对此当然了然于胸。
于是,当好心人来劝他收敛一下,不要太咄咄逼人时,他响亮地喊出了“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的豪言壮语。在底层摸爬滚打了四十几年,混得人人见了他如同见了苍蝇,连父母兄弟都不要认他,如此惨不忍睹,而他还是觍着脸儿坚持下去,不就是为了争取一张参加“五鼎食”的入场券么!既入了席,你又来劝我夹着尾巴,收着胃口,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别看我们个个在席上冠冕堂皇,锦衣绣服,望之若神仙中人,但只要皇帝那双手做一个动作你我就得退出这场盛宴。那么,哄得那双手高兴不就可以永远高踞席上大嚼了么?难!难!难!那双翻云覆雨手从来都是天意难问,岂是能轻易哄好的!再则说,入席名额有限,人人喊挤、个个冒火,你就能保证不会有人为多吃一口而借助那双手把你赶出去?因此,有了权力就要用、有了机会就要捞、有了威风就要抖、有了快感就要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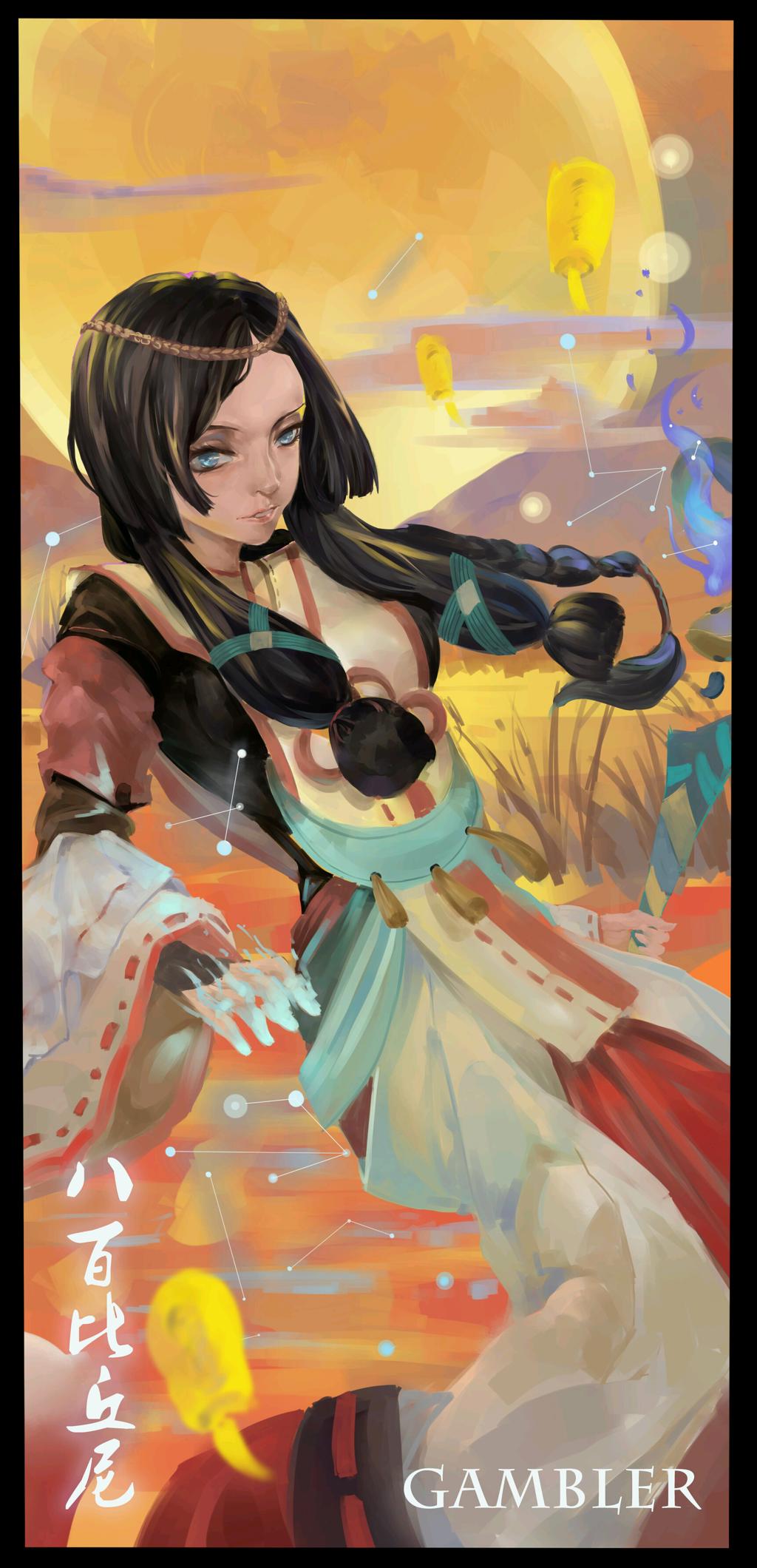
快乐的保鲜期是短暂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下个店了。如果不幸摔了跤,那也没什么,不就是“五鼎烹”么,自己还可以为食客提供一道新鲜的开胃菜。毕竟,我曾经“五鼎食”过,乐过、笑过、快意过,足矣!
他是个明白人,更是个爽快人,心中咋想就咋说。喊破了几千年来专制社会做官的真实意图,也看穿了专制社会官场上的那套把戏。因此他依然故我,无所顾忌,继续着他的“五鼎而食”。不过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他也将用他自己乃至全族人的生命去诠释那“五鼎烹”的结局。
 有崩坏三人物的聊天群小说
有崩坏三人物的聊天群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