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肉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文/赛炳文
牛肉来自滹沱,即今天的新关,在广武门内,距东城壕不远,是一个和南关历史一样悠久的回民社区。这里有兰州最大的牛羊肉市场。那时候的羊肉并不好吃,市面上常见的是一种叫洮羊的品种,膻腥味很重,连最善于烹制羊肉的回民老阿爷也畏之三分,这也可能是马保子以热锅子面起家时,没有选择羊肉的原因之一。而牛肉却十分鲜美,普遍供应的是本地产的黄牛肉,肉质细嫩,口感极佳。百年来,牛肉面的拥趸和一些不明就里的作家们乐意传播一个富于神秘气息的传说,说马保子为了独步江湖,以其非凡的才华将兰州市场上并不多见的牦牛肉引进烹饪系统,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和兰州北山的和尚头面粉加之兰州本地产的蓬灰构成牛肉面的三个独特要素,给了牛肉面一个宏大的地理背景和无可复制的人文特质,为“牛肉面一出兰州就变味”提供了一种似是而非的佐证。这一传说有力地塑造了牛肉面的地方品牌形象,也为兰州牛肉面人的固守家门提供了品质层面的借口。

20世纪初的西北,物流极不发达,市场上牦牛肉凤毛麟角,这种肉质粗糙、略有柴感的肉品并不像今天这样受人追捧。牦牛肉的香味似乎也不太符合中产阶级的味觉审美。“那种香味是扑鼻的,如果说黄牛肉刚出锅时能香飘5 米,牦牛肉则能香飘10米,像一阵轻风,倏忽不见,而黄牛肉的香味持久不散,沁人肺腑。” 一位叫黄伟国的资深牛肉面人对此有过仔细的考证,“黄牛肉煮出来的汤很清,或呈淡淡的啤酒色,而牦牛肉因为血高,煮出来的汤发红、发黑,并不符合清汤牛肉面的特点。”
熬汤是整个工序的首要环节。煮肉是为了熬汤,熟肉是副产品,是牛肉面上桌前的一点搭配。兰州回民对于煮肉有着丰富的经验,多大的火,多长时间,加什么料,什么时候加料,调料的配方,乃至加料的方法,都有着一套严苛的操作规程。如果是在各人的家里,这套规程就会因人而异,但对于坐店经营的马保子来说,规范化的操作程序是保证品质稳定的必然要求。午后是一天中最为闲适的时段,时光移动得很慢。店铺打烊后,屋里显得非常寂静,阳光从门缝里透进来,照亮空气中的粉尘,煮肉的程序在慢条斯理地进行着。从市场上买来的牛肉,先要进行仔细的漂洗,以保证其洁净。漂洗后的血水不倒,留存备用。肉要在凉水中下锅,在水将开之时,锅里泛起了沫子,这时赶快用小勺将肉沫子打掉。刚打完沫子,锅就开了,这时候就要下料了。调料都是带壳子的,一般是三样:花椒,姜片,草果。

煮肉是一个慢火熬炖的过程,时间的长短决定着汤的品质,往往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要等肉和调料里面的营养成分充分地融入汤里。这个过程也非常寂寞,时间似乎越走越慢,门外市声喧嚣,门内的人无精打采,肉汤在锅里咕噜咕嘟地滚着,肉香弥漫在屋里,灶膛里的火焰要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小,太旺则水易干,太小则营养成分不能充分融进去,煮出来的肉也不好吃。火势还要保持均匀,否则会影响肉汤的品质。整个过程就像熬一碗中药。
经过一个下午熬炖的牛肉终于要起锅了。肉已经烂香到入口即化的程度,用叉子叉了捞出,置于案板上供随后切丁,一锅肉汤漂满了一层浮油,得先用罩子再用勺子仔细地撇掉,然后把刚开始漂洗生肉时留下的血水倒入汤里,顶起汤里的沉渣细沫,这个环节叫顶沫子。顶完沫子的汤变得清澈如水,亮可鉴人。接下来就要第二次下料了,这时下的是粉料,下到锅里,搅匀,拔锅。这个环节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下了粉料后不能再煮,再煮就要变味;二是肉汤必须放在凉处晾置,使其迅速变凉,不然就会变酸。这时候的肉汤是不能喝的,调料味很重,要待第二天兑水后才能使用。

和面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程序。在牛肉面的众多传说中,和尚头面粉被赋予了一种神话色彩,其生产地的光照、土壤、气候甚至地下水都被拿来说事。在前杂交小麦时代,和尚头是甘肃黄土高原上普遍种植的旱地小麦品种,因为没有麦芒而被称为“和尚头”,其籽粒饱满坚硬,面质粉白似雪,蛋白质含量较高,因为产量低、品种过于古老而近乎被淘汰。这些品质极易引发消费主义时代的人们对“逝去的麦香”的遐想。
这种面粉在市场上最容易获得,依据品相,被分成若干个等级,马保子自然要选择最高的那个等级,这是作为理想主义的牛肉面宗师和现实主义商人的马保子从一开始就坚守的原则。面粉是不能囤积的,每天都要到市场上去买,这既符合自然主义的生活理念,也是小本经营者成本控制的有效手段。
和面的工作通常在清早进行。这时候,晨礼刚刚结束,城市尚未苏醒,从南滩街到东城壕的石子路面传递着细碎的脚步声。马保子到店的时候,贪睡的伙计还没有来。多年来,马保子已经习惯于任何事情都亲力亲为,他一直相信自己的手禀子和传说中一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若不是这双看似平凡的手亲自操作,便不能安慰食客们挑剔的味蕾。当天要用的面粉总量是固定的,要一次性和好。面粉被倒在一个盆子里,一边细细地倒水一边轻轻地划拉,水将面粉黏合起来,张力传导到手指,有一种细腻的快感。渗水的面粉在张力的作用下被划拉成索子。索子一定要拉得足够细,否则就会包水,这样的面叫包水面,连普通的主妇都无法容忍。面被拉成索子后,其分子的排列还相当混乱,无法塑形。接下来就要用力了,洒上水,使劲揉。在这一过程中,面的分子被有序排列,黏合度越来越强,柔韧性也随之增大。

等面团被揉均匀了,就需要打一点底灰,也就是蓬灰水。这时候的面团就可以放在盆子或案板上饧上了。这是揉面的第一个环节,与中国北方普遍流行的各种拉面的工艺没什么区别。
马保子的创制在于第二个环节,在开门迎客之前,从正在饧着的面上切下一块,用拳头打开,中间打出一个窝,把蓬灰水倒进去,叫窝子灰。为了防止面软,这时需要再挖一碗干面倒进窝里,然后将其蹭开,让蓬灰和干面充分地融合进面团。接下来的程序是纯粹的力气活,用拳头对面团进行反复捶捣,抻开,对折,再捶捣,抻开,对折,捶捣,如此反复。后马保子时代的兰州人形象地将之称为三捶两梆子。其实何止三捶两梆子,在这个环节上费的功夫越大,则面的柔韧性越好。所有的劲力几乎使在这一环节,就像一曲激情叙事的高潮部分,激越,澎湃,情感饱满,能量充沛,面匠胳膊上肌肉累累,青筋暴突。这一过程要持续十几到几十分钟,最后收于一段抒情的柔板,绵软柔和的面团被拉拽揉搓成条状,这一过程被称为顺筋,然后揪成几节,排列整齐,捂盖好,以备下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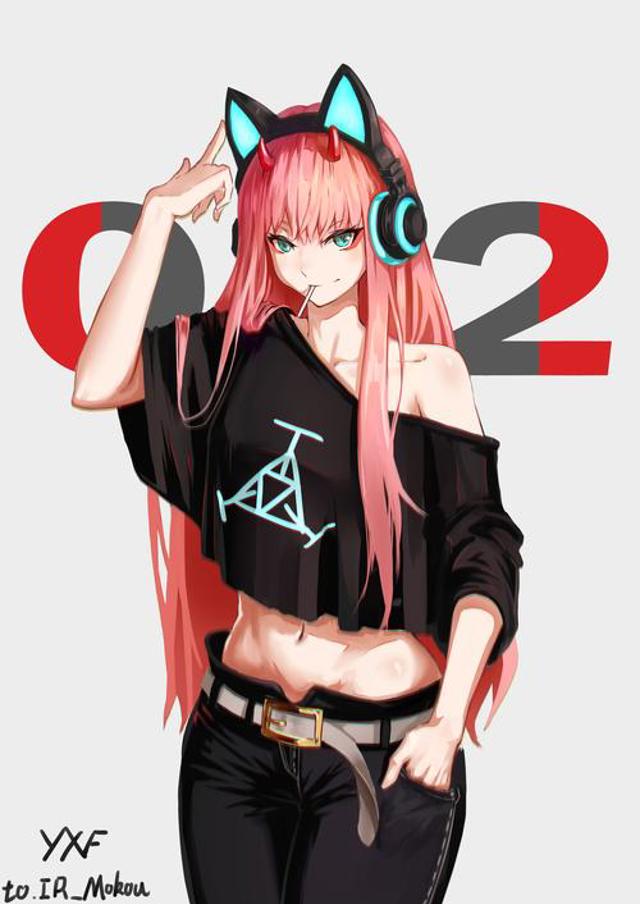
在这一叙事中,蓬灰是最为基本的一个元素。马保子并非蓬灰神奇功效的发现者。蓬灰的应用至少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在马保子时代,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人们可以从市场上顺利买到这种生产烦琐、价格低廉的东西。由于市场上纯碱的价格不菲,家庭主妇们也普遍使用这种从蓬草中提取的碱性添加剂,但其熬制过程实在艰辛。而对于面食经营者来说,这种添加剂烦琐的熬制过程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工匠精神。因此,自马保子始,关于牛肉面和蓬灰之间的关联便有了某种天启般的神秘色彩。水蓬草,一种在干旱的黄土高原上野蛮疯长的蓬类植物在化成灰烬后还能成就这样一段生命的传奇。
水蓬草在民间也被称作飞蓬、灰蓬、蓬柴,多生长于干旱贫瘠的山坡和荒滩,含碱量很高,因为其茎叶苦涩难咽,牛羊很少触碰,所以在夏秋之际,这种卑微的植物便在裸露的黄土上蓬蓬勃勃地张扬着绿意,甚至在农庄的房前屋后也多有分布。深秋的第一场霜降之后,成熟的籽粒随风飘落,深入泥土,茎叶因为失去水分而变得枯黄,形销骨立地在风中瑟瑟抖动。这时候,农闲之余的农民开始上山,把满山遍野的蓬草拔下来,堆在平缓处,接受风吹日晒。等一坡一洼的蓬草收集得差不多了,就在平地顺风处挖一个很大的灶坑,上面预留一个透空气的孔,把晒得半干的蓬草塞进去,点燃,这一过程被叫作烧蓬灰。火在熊熊燃烧,新的蓬草被不断地送进去,直到一山的蓬草全部化为通红的草木灰,热浪涌动,看起来像钢水一样的流质,然后浇以凉水,使其迅速冷却凝固,或者用湿土填埋,待灶坑完全冷却——通常可能要经过两三天——就用铁锨将这种黑色的石头撬出来,或装车或盛筐,走过长长的山路运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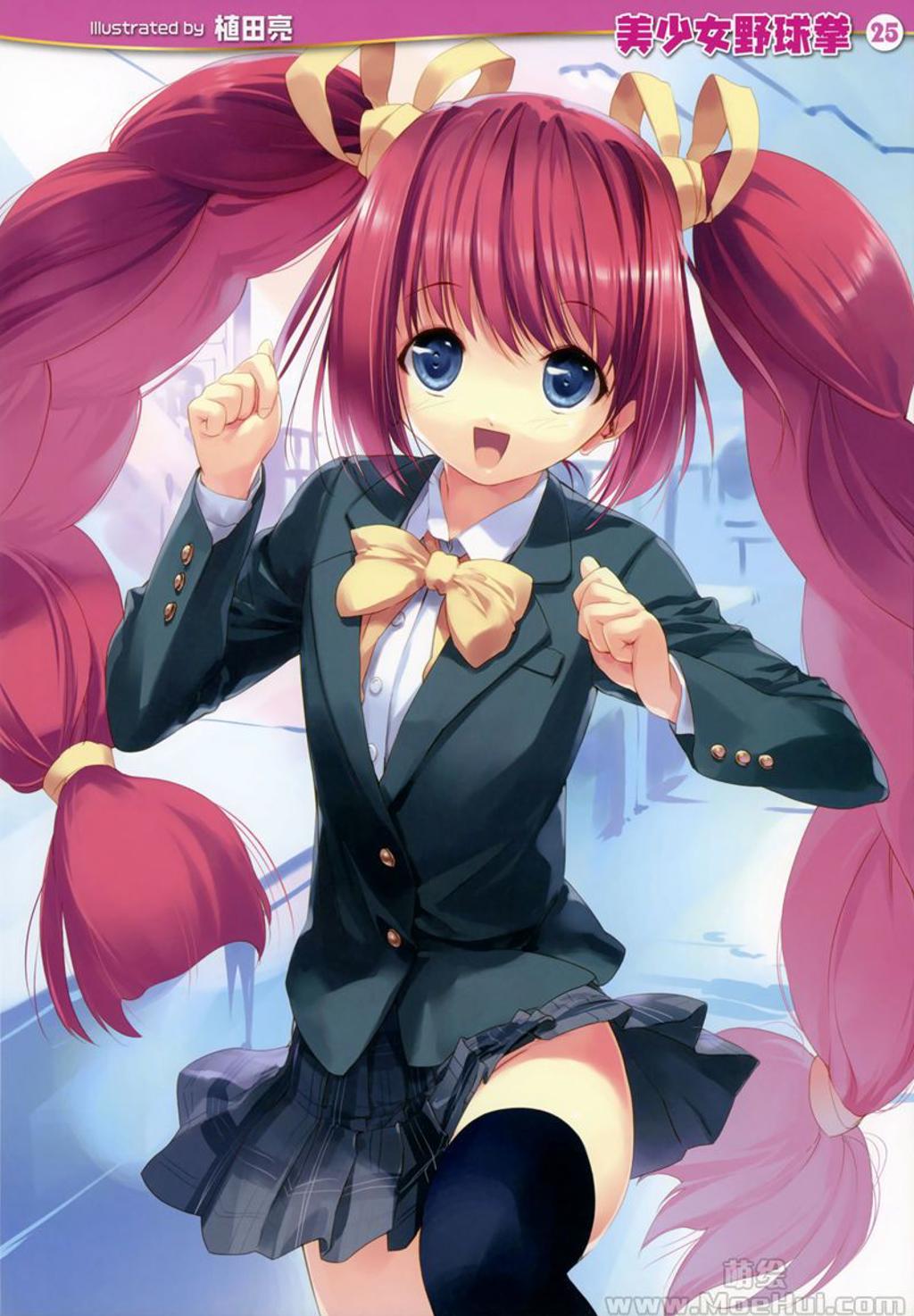
兰州诗人叶舟有一篇短文,题为《黄金在枝头转移》,以诗意的笔调写牛肉面,写得极美。这篇妙文真正想传达的,是对蓬草的致敬:
那时,我常常看见一日的买卖停当后,厨师们坐在门端里,手执铁锤,在敲打一块块黝黑的石头。石头嶙峋狰狞,大小不一,仿佛刚从古代的山崖上劈伐下来,在飞溅的火花下离析,带着旧年代里的密码。我不明白这干人在做什么,个个像艺术家,在凿试,在剥离。碎裂的石块,渐渐被碾压成了粉末,再丢进滚沸的铁镬里,在炉火上烧煮。刚刚还清亮亮的一锅汤,被煮成了泥黑的水,脱胎换骨,戽干,晾凉,珍存。师傅们告诉我:
“这是蓬灰!”
肉食者鄙。
秋风吹,山蛇肥。万木飘零之际,西北的农民们便携带了铁耙子,将旷野上的蓬草收拢回家,一半烧炕,一半点灶。蓬草燃尽后,炉膛里的灰烬,方成了这一季仅存的骨殖,蕴藏着精和气,被埋进了地下的深坑,像一场公开的葬仪。深埋三年,原本散漫的余烬,在地火和意志的催逼下,竟幻变成了一块块黝黑的顽石,被起出,被运进城里,被敲击成粉,被熬煮成汤——

是谓,蓬灰水!
……
青绿,进而焚为灰烬,达致于乌黑,终结在黄金一色。我也从少年人,混入了颠沛的中年,从一茎蓬草上,看见黄金在枝头上转移。
是谁?
——其实是里尔克,这样说过:
“我们嚼着,痛苦的拌料!”
兰州的蓬灰市场在黄河北的庙滩子,这里有连接城乡的一个农副土产市场,瓜果、菜蔬、禽蛋、中草药等不一而足,还有众多的车马店为南来北往的商贩提供着仓储和歇脚的便利。从乡下运来的蓬灰通常被堆放在车马店的墙角或床底下,大概只有进货的人可以辨识出这种黑色石头与煤炭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它的外形更像炉渣,或者炼化过的玻璃。
马保子每个礼拜都要去庙滩子进一次货。这时候,黄河铁桥已经竣工通行有六年之久,从东城壕到庙滩子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脚程,非常方便。如果资金宽裕,也可能一次性多进一些。蓬灰是最不需要保鲜的食材。
熬蓬灰水的工序叫滚灰,一般一个礼拜进行一次,每次都要耗费一个下午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滚灰的那一天就要关门歇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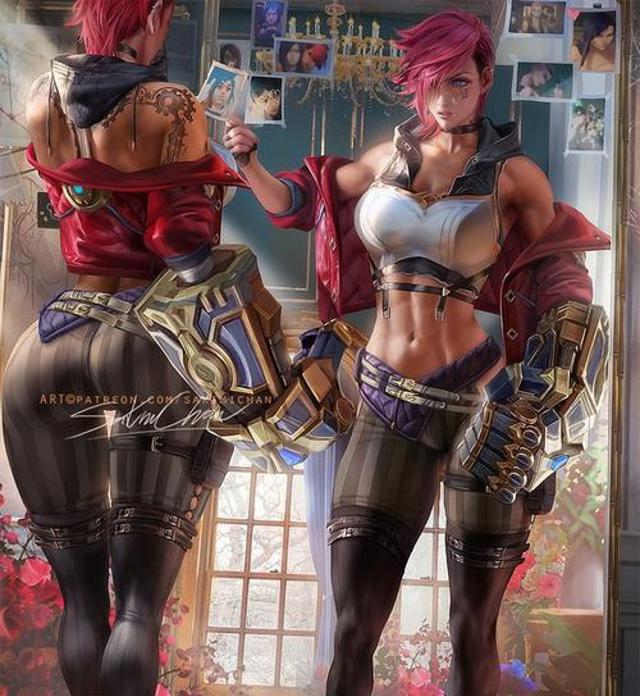
首先要用锤子把坚硬的蓬灰块敲碎,碎成颗粒比指头蛋还要小的豆瓣灰,然后放进一口大铁锅;铁锅被架在火炉上,里面盛满了水,等水开了,就要用铲子或木棒持续地搅动。这又是一个消磨意志的艰辛过程,搅动不能停止,要匀速进行,蓬灰颗粒在锅里不断地碰撞、摩擦、挤压,其有效成分以不易觉察的缓慢溶解进水里。如果搅动稍有懈怠,蓬灰就可能粘锅,其后果可能是锅底被烧穿。这是一幅毫无色彩的景象,呆板、单调、僵硬,热气蒸腾中往往是一张慵懒倦怠的面容,这张面容经常可能是伙计的,也只有在这个环节中,马保子那一双充满魔力的手可以不必亲临。
一个漫长的下午过去了,蓬灰在锅底变成一层细滑的粉末,这是不能溶解的炭,其手感就像石墨粉。所有的有效成分被溶进了水里,但那些碱性的分子是肉眼看不见的,清澈见底的蓬灰水看起来微黄淡绿,色泽令人赏心悦目,伙计疲倦的面孔这才绽放出欣慰的笑意。蓬灰水被盛放在一口专门的缸里,因为里面没有有机物质,存放一个礼拜或者更长的时间都不会有问题。

蓬灰中的碳酸钾与面团中的淀粉发生反应,给面团带来了奇妙的变化。原本洁白玉润的面团有了一层发亮的微黄,质感柔韧、筋道,尝试着拽一块下来,揉成条状,轻轻一拉,柔性和韧性恰到好处,意味着用灰的工艺无可挑剔,接下来只等顾客进店,面匠要展示拉面的技艺了。
在马保子时代,拉面的技艺并无多少观赏性,把一根小条子面搓细,两手拉开,折叠,再拉开,通过多次倒手,面条达到 了满意的粗度。有些顾客希望拉得细一些,便多折一手,反之则少折一手。拉面师的技艺体现在力道是否均匀,拉出的面条会不会断。对马保子来说,这已经像黑夜穿针一样熟练。把拉面变成一项极具观赏性的手艺,要等到两年之后马杰三上案。
牛肉汤在大锅里滚着,因为已经按比例兑了清水,使这锅汤看上去愈加清澈透亮。和肉汤一道漂滚的是雪白的萝卜片,这又是一道完美的组合,在传统的回民饮食中,萝卜通常和羊肉同煮,萝卜为羊肉去膻,羊肉给萝卜提味,二者的营养成分互相渗透,相得益彰。羊肉的温阳补肾和萝卜的益脾和胃本是一道养生绝配,若经一双妙手料理,那美满的味觉享受更是让人贪恋不已。马保子显然深得回民传统饮食之精髓,也许是妙手偶得,也许是精心设计,几片萝卜入汤,再经一番温火慢炖,简单的食材被赋予了一种高妙的品性。

香菜也是回民传统饮食中羊肉汤的标配,既为乳白色的羊肉汤增添色彩,又给鲜美浓郁的汤汁增加了一种清爽沁心的香味。如果羊肉汤过于肥腻,香菜的清爽恰到好处地起到稀释的作用,给味蕾一种更舒爽的体验。对于马保子来说,将香菜引入这一碗牛肉汤似乎不需要特别的灵感,他可能没想到的是,这一撮漂浮在清汤之上的绿色,在他之后引发了多少牛肉面的拥趸们诗意的遐想。
油泼辣子是兰州甚至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面食的另一个标配,其历史可能要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长。精心地炸制一罐油泼辣子几乎是所有主妇们的必修手艺,辣椒的使用量也无形中成为考察一个家庭饮食质量的参照,中产阶级家庭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可能要比一碟辣椒所呈现的表面内容更为丰富。从凉面和热锅子面时代传承下来的这一配置,为牛肉面的视觉形象增添了另一道诗意的想象。当然,其味觉刺激所带来的独特体验也是实实在在的,那种不调辣椒的食客会引发牛肉面拥趸们的同情,因为他们吃了一碗并不完整的牛肉面。

马保子所建立的这个系统,每一个细节都充满如此丰满的魅力,每一丁点儿的改变都可能使这个体系出现瑕疵,以至于在随后的百年时间里,从选材到出锅,牛肉面的基本结构和制作工艺未曾改变,马保子的完美设计没有给后人留下太多革新的余地。
在牛肉面诞生的最初两年里,兰州人对这种极具小资品位的面食新吃法表现得颇为犹疑。一碗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熬炖的清汤,一筷子不足以果腹的面条,被白色的萝卜片、绿色的香菜、火红的辣椒油过分装饰的色彩,在东城壕的普通劳动者眼里,这种过于精致的美食即便让人三日不知肉味,也不如一张大饼来得实惠。而在那些公务员、小职员、商行老板眼里,这碗面充分彰显了自己的阶级身份,它的审美价值远大于实用价值。
马保子,这位天才的美食设计者,他的理想主义情怀被折进时代的皱褶里,需要流淌的时光来慢慢释放。
摘自《大碗传奇 : 牛肉面传》青海人民出版社
 浅竹清韵系统
浅竹清韵系统



















